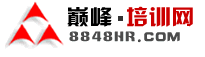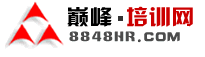文章类别: 文章类别: |
|
|
|
| |
广告:120元/月/条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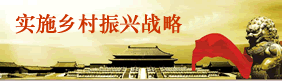 |
|
 |
当前类别 >
管理培训文库> 宗教哲学与管理 |
|
| 一个民族的背影
|
| 宗教哲学与管理:一个民族的背影,宗教哲学与管理:一个民族的背影,宗教哲学与管理:一个民族的背影,宗教哲学与管理:一个民族的背影,
|
|
| |
灾难为传统和现代制造了空前平等,借此,羌族人的古典智慧和传统生活方式展现出它们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

林川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6月15日,第二炮兵工程部队首长宣布,隔日进北川县城勘查现场,制定抢救埋在废墟下面的羌族文物方案。
自5月17日北川大撤离以来,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局局长林川和县图书馆副馆长唐成等人就在重复做着一件事,两度向县指挥部提出《到城区抢救禹羌文化研究资料及部分珍贵文物现场踏勘》的请示。
大撤离当日,已过而立之年的林川是最后一批撤出县城的人员之一。他熬着通红的双眼,死死盯着眼前这片昔日繁华秀丽、如今已成废墟的死城,怎么也不肯离开。
抢救生命的工作已结束。林川的7个亲人被永远埋在了废墟之下。逝去的生命不可挽回,但林川不甘心,他竭尽全力在寻找一些还有可能被留住的东西。和亲人残骸在一起的,还有十多年来全县合力对羌文化的保护成果。“如果没了这些珍贵的禹羌资料,从今后北川何以担当全国唯一羌族自治县这个名分?”林川说。对这个土生土长的羌族人而言,羌文化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方式。
这个参与创造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古老民族(夏禹的子孙夏启开创夏朝,而大禹正是川北羌族人),其实已经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失去固有形态,县城内的羌人不再身着羌服,生活习俗也渐被汉化。不过,数十年来,人们努力通过精神产物的传承来保留民族灵魂。位于四川绵阳市曲山镇的北川县城,逐渐成为整个羌族的文化腹地,保留了最为丰富的禹羌文化资料。但不料,今年5月12日,在四川北部,沿着理县、汶川、茂县、北川这条东北走向的斜线被撕开一道伤口,中国30万羌族人的主要聚居地惨遭不测,其中尤以汶川、北川为甚。
4259平方米的文化中心(含羌族民俗博物馆、禹羌文化研究中心和文物管理所)、7500平方米的文化馆(含艺术培训中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中心)、2200平方米的图书馆、2350平方米的影剧院、2450平方米的川剧团……现在,废墟之下沉睡着奄奄一息的文化重镇。
无法估算被埋资料的价值。北川县档案馆在震前整个库存是85000多件,其中国家重点档案有8801件,包括晚清时期文物档案100多件、民国时期文物档案8000多件,近万件馆藏羌族民俗实物、红军文物。林川回忆说,光是收集这些文物就花费了几十万元。
此外,全县文化工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包括羌族出版物、搜集整理的羌族文学、音乐乐谱、舞蹈图谱等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众多资料,以及储存在电脑里的研究资料,都随着县文化馆大楼一同被埋在地下。原县文化局的工作人员邓远海是地震幸存者,他偶然揣进裤袋的一个U盘成了震后北川县仅存的珍贵资料来源。
林川舍不得这些文物资料,他相信这是羌民族的立根之本,也是帮助28万羌族幸存者重建信心的源泉。尽管妻子被地震夺去了一条腿,躺在成都一家医院里生死未卜,林川只去探望过一次,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文物资料的抢救工作上。
撤离后,北川县政府在安县安昌镇设立了临时办公室,成立北川抗震救灾指挥部文物抢救组,林川带领着县城内幸存的几十名文化工作者迅速清点文化资产损失,屡次向县指挥部提出挖掘文物资料的申请,同时向四川旅游局要求资金和物质援助。在请示报告的最后一行,他们焦急的心情被格式地表达出来:“妥否,请批示”。
遭遇有史以来空前重创的故土近在咫尺,林川和他的同事们深知战胜焦虑的必要,这个被誉为“云端上的民族”要和灾难争夺尊严,需要足够强大的意志来忍受繁琐至极、收效甚微的挖掘工作。日复一日,伴随文物保护者的,只有上空中弥漫的亲人们的尸臭。但无论怎样,在重建文明的事业上,不仅需要官方力量,更倚仗民间社会的倾力而为。
搜索
一个月近乎疯狂的坚持之后,6月16日凌晨5点,距北川封城整整30天后,林川首次回到魂萦梦牵的北川县城内。
同行的除了两名记者,还有二炮的张西南将军一行6人,以及北川抗震救灾指挥部文物抢救组5名组员:韩贵钧、郭志武、成满德、陈志伟和陈世琼。他们是北川县城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即使在面目全非的县城,也能准确辨认出各个文化单位的原址方位。
吉普车一路颠簸,从安县境内进入北川的时候,地貌突然变成了陡峭的山区。实际上,早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就有地质学家专程前往北川考察,建议县城迁址。因为它不偏不倚恰好位于龙门山的地震断裂带上,且夹于喜马拉雅山余脉和龙门山余脉之间,这样的选址非常不科学。或许因为起源于甘孜一代的羌民族本属游牧民族,由于战争和灾难不断迁徙,在定居长江支流岷江附近以来,羌族人个性中好山乐水的一面被激发出来,他们生性守旧,再不愿离开生活多年的地方。
本来,羌族人对这个长期栖居地的“坏脾性”已相当熟悉,小型滑坡偶有出现。而这次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却多达上百处。不过,面对一片荒芜狼藉,羌族人表现出了更坚决的意志。“只要羌族人没有离开自己的村庄,羌族文化就不会消失。所以我们也会尽量原地重建。”汶川县委副书记张志宏说。然而,灾难已使地貌发生突变,寻找文物保护地的地址这项基本工作,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林川一行的汽车停在城门外,大家下车戴上口罩徒步进城。自封城以来,防疫车和直升机经常给北川废墟立体消毒,加上凌晨空气中湿度较大,尸臭味尚不明显。沿县城主干道禹龙中街向里走,只有数百米的平地,接着就看见一座庞大的高达三十米的废墟,林川指指这废墟,告诉军长,这就是整个老城区。
废墟一旁,原本六层高的财政局大楼成了一栋微微倾斜的三层楼房,整整三层沉降在地下,四十名正在一楼开会的工作人员再没有结束会议。
人们手脚并用爬上废墟,到处是龇牙咧嘴的钢筋,地震的冲击波居然将一部轿车抛到了三十多米高的废墟顶部。
终于,一名组员从废墟中发现了一大堆破碎的瓷砖,一眼认出这是文化馆内的墙砖。但是,同行的军队认为文化馆已完全被深埋,很难开展挖掘,况且在馆内仍然埋有一百多名遇难员工的尸体。
听到这个消息,林川闷着头不吭声,蹲在文化馆废墟中翻找,手掌都被刮破了。他找到了一些羌族歌舞风情碟,纪念大禹诞辰4133年文艺晚会专辑,包括一些珍贵的影集画册。新华书店、图书馆的方位也相继被认出,但等待它们的是唯一的命运裁决:挖掘难度相当大,只能保持原状。
走到邻山一棵树下,有人认出了这是以前的县委大院。县档案馆就在这个院内,原本的六层楼在地震中完全垮塌,五六根钢筋混凝土梁柱被拧成麻花状。这里的挖掘工作相对较为可行,初步方案是用挖掘机砸碎楼顶,用液压扩张器、剪钳、撑杆处理倒塌的横梁,然后由部队士兵钻进去将资料抢救出来。
临近午时,尸臭味渐浓,由于大河的阻隔,无法去新城区勘查,大家开始从原路撤离。
7月4日,抢救工作正式开始,主要是针对可行性最高的档案馆。当天,2万余件档案被抢救出来,连夜送至绵阳市档案馆进行修复性整理。
与此同时,北川县城的选址也有了眉目,新址暂定为安昌镇东南方向约2公里处的板凳桥。当挖掘工作正式启动的时候,林川为首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所有幸存者都从机器作业的轰鸣声中意识到,离歌已然奏起。

返璞归真
作为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精神产物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这能够解释为何林川和他的同行者在得知不可能抢救出全部资料时所感受到的不可言说的痛楚。不过,就整体而言,除了上述文物,羌族的碉楼、碉房、古向导、地下水网等古建筑均是民族特性的最直观体现。
在这方面,隶属理县的桃坪村寨几乎保留了最完整的羌族建筑群。桃坪村村书记张崇明一直记得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亨利博士来桃坪考察时所说的话:“他说世界上这种城堡式的建筑只有三处,一处在意大利,一处在格鲁吉亚,一处就在中国。前两处都是残垣断壁了,完整保留下来的唯有桃坪村羌寨。”在地震前,桃坪村作为羌族建筑文化的天然展示区,已是巴蜀知名的旅游地。
幸运的是,8级地震让北川人被迫迁址,而同为羌寨的萝卜寨、阿尔寨、布瓦寨也皆成废墟。唯有距震中汶川仅18公里的桃坪村寨,却一脉尚存。全村98户“格尔麦阿嘎”(羌语里指“古巷人家”)、540名羌民无一死伤。
虽有选址优势,但羌族人知道,羌寨得以完整保留的关键在于,数千年来羌人对故土不离不弃,“人间烟火”是保护羌寨最好的方式,这是普通羌民的处世原则。
“要保住家业,这才对得起列祖列宗。”庆幸之余,张崇明深感责任深重。在幸存的山寨上,族人知道,使文化得以延续的最佳方式是尽快恢复日常生活。
6月19日,汶川大地震后37天,桃坪村开始热闹起来。虽然省道国道被毁,但隔几天就会有外出工作的乡民搭乘往汶川运送物资的卡车,翻越夹金山、梦笔山、途径雅安、小金、马尔康、理县,经历20多个小时的颠簸回到家乡。
清晨6点,太阳像往常一样照耀山川河谷,族人们纷纷从帐篷里起身,在沟边用地下水网的水扑打脸庞。整个村寨安静祥和,奶奶坐在门口小板凳上给孙女盘头发,女人倚在门边绣羌族“云云鞋”,男人坐在长条板凳上抽自产的兰花烟,在乡间青板路上,小伙子们挑着扁担去从被当地人奉为“古羌圣水”的山泉口取水,自来水普及后,取圣水的道路已被 阻截。用“小琼羌家”二女儿龙小琼的话来说,地震让村人回归到了祖辈延续了千年的生活。事实上,始于十年前的桃坪旅游业是这个古老民族和现代社会相接洽的方式,但与此同时,羌族文明的固有形态也被悄然删改。
当时,从宜宾卫校麻醉专业毕业的龙小琼决定回桃坪参与这个转型,她和几个羌族姑娘身着羌服在杂谷脑河边的317国道上载歌载舞,吸引了第一波游客。
最开始走进桃坪的是一些文化研究学者。他们入乡随俗地住在族人的石头寨子里,每天早上到河沟边去洗脸,风干腊肉炒新鲜小笋是最美味的款待。那时,这些服务每天人均收取几十元钱,村民的传统生活依旧。
但后来,慕名而来的旅游者多起来,他们的要求愈发苛刻:炒菜不能放土盐,没有洗手间,洗澡不便,“其实羌族人的传统是很少洗澡,因为桃坪的气候比较干燥,又偏冷。”龙小琼深感疲惫。
旅游带来的发展使桃坪人在两种生活中挣扎。人们利用旅游收益修建自家的洗手间,但由于很多人家不舍得花钱买排污管道,粪便直接被排到地下水网中。
靠近茶马古道的桃坪羌寨,传说中是一支皇族在战争间迁徙至此,寨外有8个门,为传统的八卦布局,寨子里有31条通道如迷宫般互为联结。应战争需要,寨内设置有完善的地下供水系统,水源引自雪山,流经古堡下暗沟,在寨内组成地下水网。寨内的主要通道下面和部分人家房内都筑有暗水道,揭开石板就能取水。水网作用很大:既是生活用水,又有消防功能,还可以调节寨内气温湿度。
粪便渐渐污染了地下水网,现在没人敢喝水网里的水。但汶川地震将桃坪的电网、水网、光缆、闭路尽数撕裂,现代生活的基本保障被摧毁之后,人们意外地接触到沉寂已久的传统生活样式。
当天下午两点多钟,天昏地暗,地震刚缓便开始下暴雨,所有人都吓瘫在地上,那时候有人喊了一声:“我们要赶紧搭帐篷!”羌民们都迅速恢复了行动力,开始自救。
灾难期间,羌族人抬出了搁置已久的传统炊具铁三角,在风雨交加的日子,这个外有三只撑脚、内有三只放锅搁脚的大铁圈需几个钟头才煮熟一顿饭。
几天过后,通过收音机村民们知道桃坪并不是重灾区,于是,大家自发组织起来,把储备的腊肉、新鲜蔬菜,塞满了几十个背篓,由几十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徒步山路背进18公里外的汶川县城去救灾。
“羌族人就是这样,生存力很强,出了再大的天灾,也有足够的自救能力。”村民们的想法和小琼一样,坚守到余震结束,然后再开始考虑寨子的修缮问题。
人间烟火
做过石匠的小琼爸爸预计,地震后,石匠和木匠的工钱会大涨,因为需要修缮的羌寨实在太多了。“近些年已经涨到了15块钱一个工,盖一幢寨子大概需要200个工,请三四个工匠三个月左右可以盖完。”一个工,指的是从太阳升起干到太阳落山。
6月19日,桃坪的余震越来越少,一些大胆的村民纷纷检查自家羌寨的损毁程度。在逐渐启动的修缮过程中,人们发现了羌寨得以幸存的秘密。
小琼家是全村最大的一户羌寨,占地2000余平方米。门口的门神“泰山石敢当”依然威猛,小琼用传统的木片锁打开木门,木门丝毫没有变形,家里的木地板、每层楼之间的独木梯俱完好无损。这不禁令人称奇,已被现代建筑摒弃的木头反而是所有建筑材料中抗震指数最高的。
据说,祖先为了让族人明白团结的道理,建寨时两户人家共用一堵墙,因此整座羌寨家家相连,户户相通。据小琼回忆,地震时,所有羌寨的左右晃动幅度达到一米以上,但是主体部分很坚韧。
另外,桃坪羌寨的地基也相当稳固。掘出三四尺深的沟,在沟内用石头砌成两尺宽的屋基,再用泥浆涂抹在石片上,层层堆高。堆砌时也有技巧,石墙必须下面厚上面薄,户外的墙也向内倾斜,形成一道“鱼脊背”,这就是桃坪羌寨抗震的秘诀所在。
相比而言,此次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萝卜寨都是分体建筑,地基只有50到80公分,由当地黄泥夯成的,尽管也有数千年历史,但绝对经不起8级地震的摧残。
事实上,这种差异源于羌族人就地取材的建筑传统。桃坪最多的是石头,而萝卜寨周边只有黄土。不过,幸存的桃坪启发了地震专家对古建筑技术的重新思考。
一公里之外的桃坪村新寨,那些现代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被地震撕扯得惨不忍睹。几年前,地方政府开展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为保护桃坪老寨,在旁边规划了一片新区,地下埋有完备的进、出水管、排污管道、及光纤闭路。每家用抓阄的方式领一块地,自己花钱盖房子,以接待旅游者。
龙小琼家盖了两幢房子。现在,其中一幢占地270平方米的四层楼房全部坍塌,另一幢的大梁已经断掉。尚未完工的新寨迅即沦为一片废墟。建筑学者认为,古羌人的智慧为今后山区的抗震建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
正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长向云驹所言,灾区不会一刀切地进行彻底迁移或原地重建,除非原来的寨子处于地震核心区,或从地质角度上不适合居住,否则会尽可能地让人们回迁,因为羌族自身的建筑是有抗震能力的。
在此基础上,国内不少专家提出各种羌寨保护方案、羌文化拯救方案。尽管建筑材质的启示不可否认,但羌族人并不喜欢更多的拯救方案。“他们不了解,我们羌民住在寨子里,就是最好的保护,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法子。” 小琼的爸爸叹息道。
的确,村寨里的老人几乎个个都是羌族专家,这是羌文化一脉相承的根本所在。
保护桃坪这样的石头房子,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室内干燥,否则石头会受潮、木头会被虫蛀。小琼爸爸指着二楼屋内的半截烟囱解释说,每天煮饭的炊烟会有一部分留在屋内回旋,此外,羌人所有的文化生活都集中在火塘边,隔三差五就会在家里举行锅庄舞会,烧一堆篝火,石头寨子在人间烟火的常年滋润下,才能保持生机。
事实上,对于一个民族文明的保护,不单纯是文物资料或建筑等物质遗产的存留,文明的传承方式如何被最大限度地保持更为重要。灾难犹如一场洗礼,羌族人的古典智慧和传统生活,由此展现出他们在现代社会重焕的生命力。长期以来,这种力量在现代生活中被当作一种遗产来保护,但这也可以被解读为某种误读与忽视。如今,灾难为传统和现代制造了空前的平等,在它面前,人间烟火的古老生存智慧重获尊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