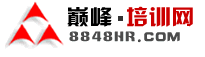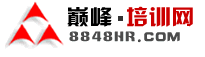|
| 后真相时代:情感与观点太多,事实和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观点。我们见过太多网络事件的反转:安徽女子为救女童被狗咬成重伤;江苏教师监考中猝死,学生平静做题;安徽女大学生称扶老人被讹……
上海姑娘刺痛着割裂的社会,罗尔让我们体验到疾病的恐怖又让我们感到人性的狡诈,被称冷血或自称被讹学生直指社会冷漠道德滑坡……
我们该怎么处理情感与事实
2016年我们已经看惯新闻反转,但罗尔事件从最初接力转发刷爆朋友圈,到被质疑炒作和诈捐,再到被指重男轻女,最后其女罗一笑因病去世,罗尔捐献女儿遗体,舆论几经反转。事实上,罗尔事件中最不缺的就是情绪,但我们对于很多细节都并不知晓,也不辨真假。
这种建立在模糊或扭曲事实基础上的感情纽带很容易因为新的事实细节浮出水面而断裂,乃至转向,然而,不管是最初的同情还是反转后的愤怒,情绪都是真实而满溢的。
《牛津英语词典》选中的2016年度词汇post-truth(“后真相”)所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简而言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观点。
还记得2016年春节期间,那件刷屏的小事吗:上海女子跟男友回江西老家过年,见到第一顿饭后想分手。
事件一出,几乎吸引了全民的关注和讨论,有人批判,有人支持,有人想讲讲自己的故事:
咪蒙:什么门当户对,不就是爱得不够;
陈岚:上海姑娘,不是逃饭,是逃命;
和菜头:上海姑娘,你的问题是没教养;
魏春亮:上海所姑娘逃离的,是我的父老乡亲们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
但就在所有人都极力带入角色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候,我们被告知这一事件其实是假新闻。事实上如果回顾事件起因,我们也会发现,这一事件所有的源头只是一则网友讲述自己经历的网帖,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信源。然而,它又是如此地“真实”:城乡、贫富割裂的鸿沟,真切地横贯在寒门子弟面前。

重要的是共鸣
咪蒙在分享其自媒体写作经验的《如何写出阅读量100W+的微信爆款文章?》一文中总道:
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众不是想看你怎么表达你自己。而是想看你怎么表达我。
我想在你的文章中看到我自己,我在朋友圈转发这篇,是因为“这就是我”“我就是这么想的”“作者帮我说了我想说的”。
所以,好的文章,要体察到人性的痛点,表达大众的情感共鸣。(注:原文如此)
深知粉丝心理的咪蒙,就上海姑娘事件写了《什么门当户对,不就是爱得不够》,希望所有女生都嫁给真爱,然而就在这一事件的三个月前她还推送了另一篇文章:《夫妻之间最大的矛盾是什么?阶级!》。
一个人也并不是决然不可能写两篇观点明显对立的文章,然而对于一个价值观早已确立的成熟写作者而言,观点立场出现急剧变化如果不是遭遇重大变故,否则必定是“另有隐情”:
你说话很温和,你观点很中立,你性格很宽容。那你不要写公号文章了。你不适合。你看了《乌合之众》就会知道,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你的标题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确。这样才容易火!
爱憎特别分明的人更适合写新媒体文章。(注:原文如此,出处同上)
谙熟自媒体写作和传播规律的咪蒙深知观点偏激才能引发读者情感共鸣,一篇《致贱人:我凭什么要帮你?!》帮读者骂了那些不管你方不方便就找你帮忙的人,然而在自己孩子失学后又当了一回贱人,请人帮忙才解决问题。

不必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咪蒙,她只是放大了情感,去引发共鸣,但在偏激的路上走得太远,难免回不了头被打脸。
不过,对于其读者(或者说粉丝)而言,在他们看到这些带有激烈观念或情感的文章时,内心一定是有共鸣而深信不疑的,不会理会这些观点或情感实际上是相矛盾的,更不管论证推理的逻辑是否经得住推敲。
后真相时代
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纷繁复杂的信息让人目不暇接,注意力早已成为各种媒体争夺的稀缺资源,自媒体也越来越娴熟地去迎合大众心理吸引点阅、引导舆论,对事实的核对、对客观的追求、对理性的崇尚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我们见过太多网络事件的反转:安徽女子为救女童被狗咬成重伤;江苏教师监考中猝死,学生平静做题;安徽女大学生称扶老人被讹……
最初,每一起事件都是在情感诉求中形成舆论共同体,然后,又在新的事实出现后突然转向。当我们事后置身事外思考时,会突然发现我们当初所置身其中的环境是如此地荒诞,当初越是确信不疑,这种荒诞感就越是强烈。
让我们争论不休的上海姑娘根本就不存在,让我们接力转发捐赠的罗尔名下还有几套房,被我们骂冷血的学生当时就采取了措施,安徽女大学生称被讹则恐怕永远是罗生门。
与其说我们是在看新闻看文章,不如说我们是在寻求情绪的共鸣,而这些事件和文章都恰好适时引发了共鸣。
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或者说是别人希望我们看到的
《乌合之众》写道: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
上海姑娘刺痛着割裂的社会,罗尔让我们体验到疾病的恐怖又让我们感到人性的狡诈,被称冷血或自称被讹学生直指社会冷漠道德滑坡。
这些单纯而强烈情感的力量~当然比现象背后复杂多维的社会现实更富有传播的魔力。
传播中需要的是这些符合情感信念的事实。
情感的需求太强烈,事实都不够用了。
……

纽约时报:西方进入“后真相政治”时代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月24日发表题为《后真相政治时代》的文章称,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当中,事实占有神圣的位置。每当民主似乎跑偏,当选民被人操纵或者政客躲避问题,我们都诉诸事实。
事实如今无力支撑共识
然而,事实似乎渐渐失去支撑共识的能力。美国“政治真相”网站发现,唐纳德特朗普70%“基于事实”的声明其实属于“基本不实”“不实”和“胡说八道”。
有关英国脱欧公投,脱欧派声称:欧盟成员国身份每周使英国损失3.5亿英镑。但不去说明英国反过来得到的资金与好处。
这种感觉现在非常普遍:我们已经进入后真相政治的时代。
当政治变得越来越充满对抗并且由电视表演主宰,“事实”就会在公众辩论中的地位升得过高。我们对真实统计数据和专家证词寄予厚望,使真相不堪重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事实”现在已经不能冷静地坐在政治争论的冲突之外,而成为冲突之内的舌战武器之一。
当事实不再被传媒和大众认同成了现实,我们还讲什么“事实”?问题在于,专家和参与提供事实的机构激增,而且这些专家和机构很多都待价而沽。如果你真想找到一位愿意为某个事实背书的专家,并且你背后有足够的金钱和政治影响力,你大概就能找到。
民粹主义运动与社交媒体的结合常常被说成是后真相政治的罪魁祸首。个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围绕自己的观点或偏见决定如何消费媒体,民粹主义领袖也乐于鼓励他们这样做。
事实权威衰落已久
但是,如果只聚焦最近事件对事实明显的滥用,那就忽视了一点:“事实”的权威其实已经衰落了很长时间。报纸或许帮助抵制了民粹主义的煽动宣传,但它对更大范围的事实危机没有任何作用。
主要问题在于,21世纪的“所谓事实”已经供应过剩:太多的来源,太多的方法,可信度各不相同,取决于谁给某项研究出资以及那些夺人眼球的数字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
文化史学家玛丽普维说,用事实描绘社会的倾向最先见于中世纪晚期,伴随着会计学的诞生而出现。普维博士认为,商人记账的新鲜之处在于,它呈现出一种看来可以独立存在的真相,无需阅读者的任何解释或信任。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会计学之外又有了统计学、经济学、测量勘查和其他一系列数字方法。但是,尽管这些方法发展扩大,它们仍然往往是结构紧密、能维持相关标准的小型机构、学术社团和专业协会的专属领域。
上世纪,一项围绕事实的产业诞生了。市场研究公司从20年代开始展开市场调查,并在30年代扩展到民意调查。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以后出现了美国企业研究所这类智库,把统计数据和经济学用于政府政策的设计,服务于这种或那种政治计划。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自由派政客当中流行一种思想,称作“基于证据的政策”,这时的经济学严重倾向于为政府计划辩护。
“事实”这个词当然不只限于数字。但它的确暗示某种可以公开分配、无需不断证实或解释的知识。
“数据社会”趋势难挡
但是,后真相政治还有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对社会产生的变革作用可能就像500年前的会计学一样巨大。
我们正处在从“事实社会”向“数据社会”转变的过程。在此期间,围绕知识和数字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存在诸多困惑,这加剧了真相本身将被遗弃的感觉。
要理解这种转变,首先需要了解“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因为兜里的智能手机和智能卡、社交媒体的惊人崛起、电子商务作为商品和服务购买方式的流行以及感应装置在公共领域的普及,我们的日常活动留下大量数据。
像统计数据和其他传统事实一样,这些数据是量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史无前例的规模(大数据里的“大”)和它们不断地被默认收集而不是在专家有意设计的情况下被收集。数字产生的速度远远高于我们能找到它们具体用途的速度。尽管如此,你也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了解人们如何行为,怎样思考。[/b]
讲“事实”有可能解决视角对立之间的争论,把问题简化。但是讲“数据”,比如政客们可能对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正确观点各异,但他们如果认同“经济增长了2%”而“失业率为5%”,那他们至少就有一个共同认定的稳定现实可以为之争论。
数据其实也用于“情绪分析”
相比之下,数据有可能感知公众情绪的变化。比如,用算法分析推特就可以获得几乎实时的最新数据,了解公众如何看待某位政客。这就是所谓的“情绪分析”。
这有例子,比如总统电视辩论中监测现场观众反应的“蠕虫曲线”,随着候选人的言论在观众中产生的反应上下波动。金融市场体现交易者在一天里不断波动的情绪。股市不可能像会计那样提供显示思科系统公司价值几何的事实,但其提供了一个窗口,显示全世界成千上万人对思科系统公司的态度每分钟如何变化。
记者和政客不能忽视对集体情绪的不断审查,正如首席执行官不能忽视公司股价的上下波动。如果英国政府拿出更多的时间设法跟踪公众对欧盟的情绪,而不是重复英国经济可以如何从欧盟成员国身份中获益这个事实,那么脱欧公投可能是另一番局面,政府也可能更成功。
脱欧派活动者之一多米尼克卡明斯嘲笑他所说的过时的民调技术。他还要求一个民调机构加入有关“热情”的问题,并且雇用科学家开采最新的大数据集,以衡量选民的情绪并通过广告和志愿者采取针对性的行动。

生活在数据而非事实的世界里是可能的。想想我们如何利用天气预报:预报说,周四的温度将为75华氏度,我们知道这不属于事实,因为数字将随时波动。天气预报的原理与情绪分析相似,通过大量感应装置收集数据,然后把这变成对不久将来的会持续发展的描述。
但是,这给政治带来某些令人恐惧的可能性。数字一旦被看做是当前情绪的指示而不是对现实的说明,我们该如何对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性质达成共识,更不用说解决方案?
这种环境导致阴谋论盛行。我们虽然有各种办法弄清有多少人相信这些理论,却没有什么办法说服他们放弃这些理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