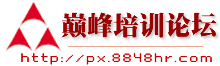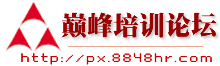| zgzx1 |
|
|
| 等级:论坛骑士(三级) |
| 积分:2436分 |
| 注册:2009-5-20 |
| 发贴:744(436主题贴) |
| 登录:1154 |
|
|
| “高考公平”和“教育公平”,是一回事吗? |
“高考公平”和“教育公平”,是一回事吗?
昨天,我们推送了这样一段话: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似乎是很有道理。 但也有人说,“这表面的合理,实际上掩盖着深层的谬误。因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程序公平,而非实质平等,它可能掩盖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
目前,普通教育阶段学校分化严重,加上普遍存在的择校制度,对于没有条件接受优质教育的社会阶层而言,高难度的入学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进入高校的屏障。”
这段话引发了很多读者给我们留言,与我们进行讨论。
从大家的留言中,大致可以分出以下几个阵营:
1、“分数面前怎么会人人平等?同样的分数,有的地方上北大,有的地方一本都上不了。”
2、 “教育或者考试,早已不是简单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即便在文革时期推荐上大学,依旧是政治处于第一位。到了现在,教育已经不再是孩子个人的事情,早就成了家庭乃至家族、阶层的事情,拼的是综合素质和综合实力。所以,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人才了。”
3、“教育改革年年都在提,可为什么迟迟不开始呢?开始都这么难,可见改革成功依然举步维艰。”
4、 “天下哪有一个制度没有漏洞?任何时候都有人成为制度的牺牲者。教育就像生病与立税,逃避不了。哪怕人人痛恨,但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我们也只能期待中国的教育制度能越来越完善。”
5、 “即使不平等,还能有什么办法达成平等呢?就像法律条款,基于人和人能创造的价值不同这个前提,民事纠纷中的赔偿项目都会按照户籍标准来确定。分数和录取标准,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6、 “这话是针对北京上海相对其它省份的高录取率而说的。这个情况与今天因教育资源日趋分化而造成的寒门学子进阶通道越来越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情况,今天的分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类似在西方国家早已形成的阶级固化。而北京上海学生入学率高则恰恰相反,是中国集权政治集中经济的结果,是掌握更多权力的阶层直接制定政策向自身利益倾斜而造成的。这种不公平不是经济差异造成的,而是权力差异造成的,也就是人们长期以来垢病的对象。中国处在社会改革转型社会阶层复杂的时代,高考政策同样面临复杂的问题。“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和照顾寒门学子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两个方面。 “
7、 “人可以实际一点,先谈生存,后谈理想。学一门技术,有时会更容易在社会立足。可是现实是,中国家长都认为考大学才是第一等事,骨子里对于读书从政的崇拜,以及对职业专科学校摒弃,都让他们认为学技术只能是次等的选择,社会的导向也同样如此。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这些家长该做什么?怎样才能为孩子的未来铺路?”
8、 “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如果按人口比例划定名次,那么就对从小面对激烈竞争的大城市孩子,显得不公平了。对一拨人公平,那么对另一拨人就不公平了,这就看国家如何取舍。”
9、 “中国因为科举文化的影响,加之家长们都希望孩子接受最好教育的初衷,势必存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但中国的高考,已经相对于许多国家很公平。现在依然有不少底层的孩子,通过努力,在高考中改变人生轨迹,实现了阶层的晋升。尽管现在还存在不公平,可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说明国家意识到了不平等,在逐渐做出改进,只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措施,在稳定各个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将社会资源公平地调配。”
10、 “教育公平,应该从受教育的初始阶段就开始。可是现在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择校,家长认定’读重点小学,才可以进入重点中学,才有希望读重点大学‘。这也导致了城乡、城市内的教育资源不均衡加剧。“
11、 “要实现教育公平,不仅需要国家从制度上引导、改革, 还需要中国家长改一改观念。”
12、 “不仅仅是高考,高考背后承载着一个家庭的资源、财力、文化水平,孩子们在参加高考前就已经有高低之分。所以要追溯不平等的根源,就要从背后这些因素去看。”
13、 “比起中国,美国的阶层分化更明显。优势资源掌握在富人手里,富人孩子可以去读收费昂贵的私立大学,而穷人社区则吸毒、流浪、性交易泛滥,孩子们很难不受影响,且也没钱去读好大学。底层人要想提升社会阶层,看起来比中国还要难。世界上没有公平。”
14、 “不应该总拿出身说事,多拿努力说事。高考已是贫苦孩子改善出身的最公平之路,分数面前就是人人平等。难道还有更平等的形式吗?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为下一代努力奋斗。“
总结起来,读者们对于“分数面前是否人人平等”这个论题,站在“很公平”、“不公平”、“相对公平”的三个阵营中。
其实,说“很公平”的人,着重点在于“高考是否公平”;而说“不公平”的人,着重点在于“录取政策是否公平”,以及“教育资源是否公平”;说“相对公平”的人,更多是着眼在“不存在制度的绝对公平”,以及“不同利益阶层的人有不同的诉求,无法全部兼顾”。
“高考公平”和“教育公平”,其实并不是同一件事。
关于高考的公平性,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也多次表示,对于普通阶层的人来说,高考确实是很公平的进阶路径。且在中国,考上名校、且上得起,又顺利毕业的几率,要大于美国、德国等国家。我们从未否认高考的公平性,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看到,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以及择校问题的扩大,正在导致教育体制内的另一面不公平。
当我们作为一项制度或政策的获益者时,是否也应该将眼光放远一点,看到正在遭受不公平的人群呢?或许,如果这些不公平的问题未得以解决,谁又能保证,未来我们的孩子参与到教育体系时,不会被这样的不公平影响到呢?
而能够收到读者这么多有见地的反馈,也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也能够从大家的观点中,受到很多启发,获得新的感悟。
教育承担着两种功能:提高能力,改变社会地位。而能力高的人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这无疑是合理的。在现在社会激烈的竞争中,后者的作用逐渐压倒前者,也就导致高等教育成为了人们获得理想身份、提高社会地位的根本性条件。
而优质的高等教育,往往是有限的。所以,这项数额有限的社会需求,却吸引到了大大超额的社会成员,注定有人能够得到优质的教育机会,而有人不能,因此也就有了如今“教育公平”的诉求。
“教育公平”从来都是个非常复杂又宏大的话题,教育的不公平,间接导致了高考不公平的存在。而以我们自身对于教育的不全面了解,还无法透彻分析出其中根源,以及给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最近,我们也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和书籍,希望从中摘取出一些可能不错的办法,与大家一起分享和讨论。
目前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普通人除了被动顺应和主动逃离,似乎无法有明确的办法。但就像很多读者在留言中提到的, 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教育现状的公平,应该更为行之有效。
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以及直辖市和省会等大城市,呈现出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中心城市和地方城市之间的较大差距,这主要是历史发展形成的巨大差距。近年来的国家政策,也在有意识地调整资源配置,在西部开发时优先发展教育。但已存在的差距,似乎仍然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正如很多读者提到的,城市和农村的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几率的不平等,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
前段时间很火的“海淀拼爸”,在他写的文章中,他坦陈儿子和女儿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上补习课,并参加各种兴趣班,平均每年每人花费十万。
每到周末,家长就要开着车带孩子马不停蹄地上课。据他所说,这样的高强度学习,不但没有遭到孩子的抵制和反感,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孩子的兴趣。孩子主动提出要继续学习,家长也乐得持续投资,无疑是一种良性循环。
而很多小城市或农村的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并无法得到这样高密度、多方位的兴趣刺激。哪怕是孩子可能有兴趣的项目,如果家长没有意识或没有条件投入,孩子的能力也得不到进一步开发。
除了学校外的能力发掘,师资力量的不均衡,也导致不同地区的孩子,在学校内所受的教育都存在质量差异。
在我们推送了《读书致贫》的文章后,有的读者留言:
“有的孩子与其在高考的独木桥上,与千军万马一起竞争,不如早些学得一门实用的技术,先在社会扎稳脚跟。尤其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成绩并不好,也明知读书致贫,他们和父母坚信‘读书改变命运’,举家借债也要继续读书。而学历价值的缩水,又让他们毕业无路。如果早点放下执念,去接受职业教育,或许来得更实在。”
这样的观点,我最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先生的作品《吾国教育病理》中,读到了相似的观点。
他在书中提出问题:
面对中国教育的激烈竞争,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什么?
首要的是缓解竞争,其次是选拔手段避免单一。
而缓解竞争,不外乎两条思路:
其一,扩大招生;其二,减少高考中的考生数量,进一步说,较早分流,将一部分潜在的考生疏导到职业教育上去,降低高考的竞争强度。
第二条思路,如果用更为学术化的名词来概括,就是“教育分流”。如果用更通俗易懂的词语概况,也就是“因材施教”。
教育分流,意味着将不同能力的学生,置于不同水平、类型的学校、班级或课程,使学生接受与自身能力水平相适应的教育,以具备将来从事某职业的能力。教育分流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学校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调整授课内容和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教学效率的最大化,这样更有利于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利用。
正如《哈利波特》中,新生进入魔法学校后,需要先寻找适合自己的学院,而这个过程,是通过一顶“分类帽”来完成的。这顶帽子会分析学生的性格和禀赋,分配给他们最适合自己的路径。
而现实中并没有如此简单的“分类帽”,如果仅用考试来决定人的出路,也不免有些简单粗暴。
所以很多国家,包括德国、英国、日本,以及芬兰、瑞士等北欧国家,很早就开始做了教育分流的尝试。
可也正如所有制度一样,教育分流的措施,也会遭到人们的质疑。
质疑的焦点,围绕于分流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有效性,即教育分流是否是比其他教学方式更有效的措施?而公平性,在于有人怀疑,是否存在学习能力和兴趣以外的因素,影响分流的过程;以及是否所有学生都能从中获益。那些进入职业学校的孩子,是否和进入学术型大学的孩子一样,能够获得同样的生存机会?
在中国,我国目前初次教育分流的时点,大约在学生15-16岁(初中升高中)的阶段。然而,因为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分配不均,以及择校情况的存在,无形中造成了学生在更早的阶段,无意识地参加了“早期分流”。
针对这个问题,郑也夫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坚决地消除重点小学和初中,方法是各所初中和小学,在硬件上摆平,教师定期抽签流转。师资流转制度能够保证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能在享有师资这一方面,站在同一起跑线,这也有助于筛选人才,因为它避免了‘伙食差别’掩盖身体潜力。因为效果上的平等,比减负更为确定,准确地说,取消重点小学和初中,更属于教育平等的追求。“
到了初中以后的中等教育阶段,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在招生规模上相近,而中职教育在时下的观念中,仍然被视为一种“次等”的选择,学历也被广泛家长和学生认为是更“实在”的硬通货。
可目前广泛存在的“毕业即失业”,也使得人们开始反思:学历究竟有那么“硬”吗?
再次套用郑也夫先生的话,
“学历是很多人趋之若鹜的需求,进大学或许不是最终的愿望,却是必要的环节。学生和家庭的需求、大学的扩张、政府的倡导,也让人们竞相开展对学历的竞争。”
对于人们普遍讨论的“学历是否加强社会阶层见的流动”,郑也夫先生也在书中给出了“不乐观”的答案。
原因在于:
“七八十年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较好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后这一作用何以削弱了呢?因为生物世界的特征,就是博弈。一个制度建立初始,与其延续的过程是大不相同的。
初始时大家都天真无知地应对,其后则是精心谋划各自的策略,以求成为现存制度中的适者。大家都要策划,当然是权势阶层更有办法。这是人类的通则。
中国的特色是,在博弈中,我们的政策缺乏弹性,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调整,且严重偏袒权势阶层。教育体系的不断扩张,使统治者和社会上层,能够通过教育满足公平、合理、增强社会流动性等社会要求,给更多处于劣势的群体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又不损害社会上层在这种教育体系中的既得利益。“
也许这也就解释了,读者关于“教育改革为何迟迟不见成效”的疑惑吧。
今天的文章,也是我读过读者反馈后,获得的启发和感悟。因为最近发现郑也夫教授的《吾国教育病理》这本书,回答了颇多我久久思索、而得不到答案的问题,所以今天也引用了他书中的论点。
在这本书中,他也回答了“为什么毕业生找不到好工作?为什么企业招不到好人才?为什么学校忙于各项评比?为什么教师喟叹职业尊严?“等问题,书中也不乏“素质教育是逻辑不通的昏话、高校扩招是通吃社会各阶层的障眼法、独子政策是高考热无法降温的根源……过度复习是摧毁创造力的利器、意志力的缺乏是当代社会的精神癌变、科技史是打通文理的金桥…”之类犀利的论点,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读一读哦。
如果您对“教育分流”感兴趣,我们会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分流制度成熟的德国,是如何解决不同能力水平学生的出路问题。
写在后面
有读者说,我们这群人作为高考的既得利益者,因为高考改变了命运,进入了好大学,为什么现在又在这里说教育的不公平?我们承认高考的公平,但也愿意发掘教育体系内的不公平。无数家长正在焦虑而无奈地被裹挟在拼娃、刷分的大潮中往前赶,生怕疏忽一时贻误孩子未来。
而正如我们在《焦虑的中产家长,为什么总是爱孩子爱过头》中所说,现在的一批中产家长,大部分是高考的获益者,但他们能够让孩子继承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因为自己的学历和社会地位,并不能直接由孩子继承。
所以他们也渐渐看到了中国教育体系不合理的地方,但因为大部分人的孩子还需要在这个体系中摸爬滚打,他们只能努力付出,帮助孩子适应现在的教育体系。可以想象,未来的社会竞争,将远远激烈于他们从前所经历的竞争,而如果教育不公平加剧,强者利用更多的资源投入教育,弱者更加束手无策。
我们的孩子,是否更有可能受到影响呢?
|
|